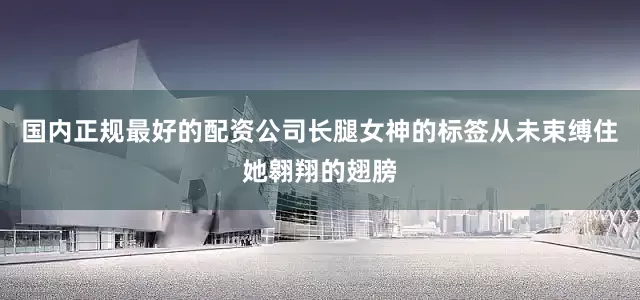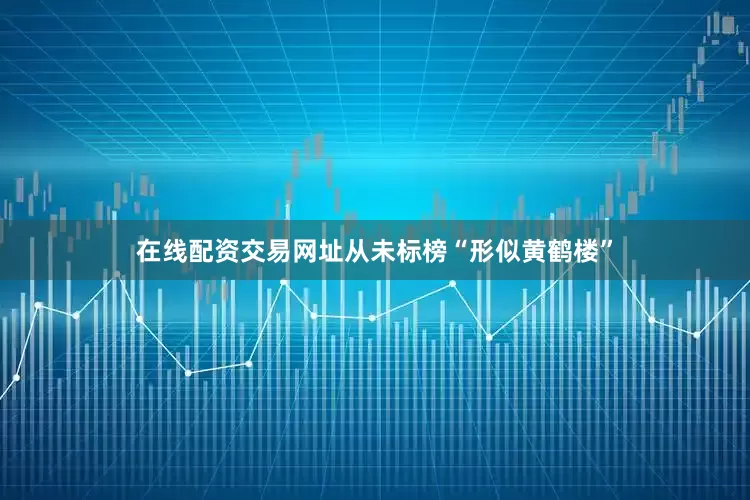
站在大别山区淠河总干渠源头的青石板上,晨雾正从水面抽离。风掠过渠边芦苇,送来湿润的土腥气,混着远处水闸启闭的嗡鸣。抬眼时,清源楼的飞檐突然刺破雾霭——青瓦如鳞,檐角铜铃串成弧,风过处,碎响里竟缠着淠河千年的涛声。友人说“这楼仿黄鹤楼建的,形制几乎分毫不差”,我却在触到木质廊柱的瞬间怔然:新漆的光泽下,木纹里似藏着个约1900年前西哲提出的古老命题——忒修斯之船,若换尽木板,还是原来的船吗?

武汉黄鹤楼,我是在一个梅雨季登临的。长江水卷着六朝云气漫过矶头,崔颢的诗碑在雨幕中洇成墨色。拾级而上时,钢筋水泥的台阶泛着冷光,檐角铜铃与江风碰撞,碎响里竟听不出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的苍凉。更惊觉的是,为让道长江大桥,楼址北迁一里,远隔沧浪后,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韵味不见了,只剩导游扩音器里的机械解说。
可崔颢笔下的晴川芳草,总在每个春天从龟山脚下返青;汉阳古树的年轮里,仍刻着“历历”的执念;江心那朵白云,依旧载着“悠悠”的古意飘进游人镜头。
古建的“形”可以坍圮,文化的“魂”却活在诗句的褶皱里、记忆的年轮中、一代代人的心跳里。当我们吟诵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,刘禹锡的乌衣巷便永远停驻在六朝烟雨中,燕子的尾羽扫过王导谢安的屐痕;当我们念起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,杜牧的扬州总有玉人在廊下燕歌,琵琶弦上跳动着晚唐的月光。反之,有些地方复刻的埃菲尔铁塔,霓虹映着塔身,却载不动巴黎左岸的咖啡香;有的公园立的“狮身人面像”,风沙漫过仿造的纹理,也寻不到底比斯城的朝阳——没有文化基因的薪传,再逼真的复刻也不过是一具空壳。
那清源楼呢?是不是也只是逼真的复刻呢?六安的友人特别说明,当地在宣传清源楼时,从未标榜“形似黄鹤楼”,而是始终强调这是淠史杭工程纪念馆。
拾级登上清源楼,木栏上的包浆还带着新漆的涩。七大展厅的灯次第亮起时,大别山人凿山导淮的老照片在墙上游走:钢钎扎进岩缝的瞬间,石屑迸成雪;夯土的号子声从喇叭里漫出来,与檐角铜铃的脆响绞成一股绳。玻璃柜里躺着20世纪的夯具,木纹间浸着当年的汗渍,握把处的凹痕,分明是某双粗糙的手磨出来的。
在展厅最深处,一张泛黄合影突然拽住我的目光:数十个青年赤着上身,钢钎扛在肩头,背景是炸开的岩壁,碎石像雪片落满衣襟。解说的声音轻下来:“这是当年淠河干渠工地,这些敦实的汉子是夯土工。”我盯着照片,解说停顿了一会复又响起:“当地庆祝淠史杭开工60周年时,曾寻访过这些人,他们说钢钎扎进岩缝时,石屑溅在脸上像撒盐。”
展柜里,有柄包浆厚重的夯具,“当年开山,钢钎钎杆冻手,他们用布条缠了又缠;雨夜夯土,蓑衣盖着夯具,号子声压过惊雷。有回粮票断了,全村人把自留地的山芋往工地送,山芋藤在渠边堆成小山。”
我隔空摩挲夯具上的刻痕,指尖仿佛划过他们当年手掌磨出的血泡厚茧——突然懂了,淠史杭的史诗从不是冰冷的数字,它是钢钎上的布条、山芋干酿的酒、雨夜夯土的号子,是无数双布满血泡的手,把“人定胜天”的信念夯进泥土。而眼前的清源楼,正是这些血泡与刻痕垒成的碑。
登临此处,风过檐铃时,恍惚间能听见淠河水闸启闭的齿轮声,大别山开山凿石的铁锤声,开凿干渠时夯土的号子声——这些声响,铸就了另一艘“忒修斯之船”的龙骨……这时候才惊觉,楼的飞檐虽借了黄鹤之姿,脊梁里却撑着另一种史诗:不是文人墨客的烟霞,是农夫与工匠在山水间劈开的生路。
暮色垂落时,我站在淠河码头,看清源楼的轮廓与记忆里黄鹤楼的剪影在水面叠成双影。长江的浪、淠河的波,各自托着文明的舟。
股市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